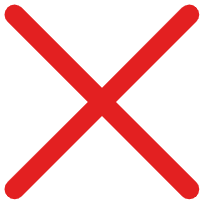400-040-0988




根据《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可知,追加原股东作为被执行人的充要条件是“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对于“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理解,本文中的“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属于广义观念,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和未适当履行出资义务,中恒信律师事务所太原分所崔继梅律师对以下几种情况分别进行解析:
一、对于已届出资期限,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应属于“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
对于出资期限已经届满,公司原股东仍将股权对外转让的情形,此时无需区分股权转让时公司是否对外负债。公司原股东在此种情形下已不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股东在负有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转让股权属于“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公司原股东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
二、对于未实缴出资的股东在出资期限未届满前转让股权的行为是否属于“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应着重关注债权债务产生的时间节点。
关于在出资期届满前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持“转让合同绝对无效说”的学者们认为“原始股东出资不到位本身即是违法行为,违法的出资不能转让,否则转让行为应该归于无效”。崔继梅律师认为,虽然该观点的提出是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正式确立之前,将股东向公司履行足额出资义务作为获得股权的对价,认为股权的原始取得应以投资者向公司适当履行出资义务为必要条件。但在股东资格的取得与股东是否实缴出资到位之间建立起了非必要的联系和对等关系,也与《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规定相悖。股东是否履行足额出资义务,并不影响股东资格和权利的取得,否则所谓的出资期限利益仍然只是纸上谈兵,无论是在实缴制还是认缴制下,股东权利并无二致。因此认可股东在未届出资期限前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是必要的,享有出资期限利益的股权可以依法转让。
三、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下能否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
《九民纪要》第六条中规定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该条的立法本意和精神也是旨在约束公司现股东,其中包含股权的受让人,而非无限制地追加公司的原股东和发起人。在完全认缴制下,因股东期限利益的存在,公司资产仅在特殊情形下才能加速到期,公司资产常处于不充盈的程度。股东转让出资未届期股权后,在符合上述特定条件时,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后手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无论其股权所负载的出资责任是否届期。但作为前手股东应否连带承担相应责任,实践中一般持反对态度。
首先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仅在纪要文件中进行规定,《九民纪要》虽对司法实践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但位阶较低还未上升到法律层面,执行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效力,这在未来的立法工作中值得去正式确立。
其次加速到期制度虽然进一步提出在两种例外情况下,债权人享有的救济途径,但就该条来说是否包含股权转让的原股东仍未予以明确和细分。单从字面和语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应当只包括公司的现股东,原股东转让股权退出公司后不再具有股东身份,丧失股东资格和权利,有关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信息也进行了变更。加速到期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具有股东身份并且享有出资期限利益,此时原股东显然不是该制度的适格主体。站在制定者的角度分析,这一制度是为了弥补公司认缴制度的缺陷和漏洞,防止现有股东滥用期限利益,推脱责任使债权人受损害,若将该制度溯及到原股东明显作了扩大解释。
再次公司股权变更后,通过工商登记备案等制度对外予以公示,债权人对公司的股权架构、资产状况应当有所了解,负有一定的注意和谨慎义务,是否与公司发生贸易往来,主动权掌握在债权人手中。债权人应当知晓凡是涉及商业交易,风险也就相伴而生,如果可以无限制地追加公司的原股东,甚至是经过多手股权转让环节的前手股东,显然也不利于维持交易的稳定。